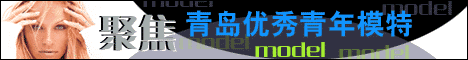“扇子扇涼風,扇夏不扇冬。”然而古往今來,寒冬臘月,大雪紛飛之時,仍手揮扇子的,也頗有人在。
你看舞臺上的諸葛亮,在明明發生于隆冬季節的《斬王雙》中,也是羽扇輕搖,風度翩翩。不知何時起,羽扇成了舞臺上智慧計謀的象征,連劉伯溫也一年四季少不了它了。
實際生活中的諸葛亮,手上所持,并非“羽扇”,而是“毛扇”。宋版《藝文類聚》引晉人裴啟的《語林》云:“諸葛武侯與宣王在渭城將戰,宣王戎服以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王聞而嘆曰:可謂名士矣!”諸葛亮搖的不是“羽扇”,而是“毛扇”。宋版《白氏六帖事類集》與《太平御覽》,也均作“毛扇”。清朝孔尚任的《桃花扇》,“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孔尚任寫此劇的15個寒暑,桌上總放著一把山東特產“魯縞”制的扇子,扇子畫著桃花數朵,猩紅如血。每當他寫到桃花扇時,總會情不自禁地端詳一番。有次正逢大雪紛飛,舉人孔尚鉉去看他,見他一手使勁揮扇,一手奮筆疾書。孔尚鉉不禁嘆曰:“手上搖著桃花扇,筆下寫著桃花扇,可謂如癡如醉,嘔心瀝血!”
李鴻章是個不懂外語的外交官。由于閱歷很深,經驗豐富,外交應酬倒也應付自如。他有一個訣竅,就是臨時抱佛腳。在會見外國使節前,匆匆學幾句該國語言,無非是寒暄客套,你好再見之類,記在肚中,說在嘴上,倒也靈驗。
某年冬天李鴻章要出使沙俄,無奈之中,取出折扇,要人在上面寫幾句俄語的音譯和意譯,而且要把譯文編成有一定意義的諧音文字。據說,扇面上的譯文有以下幾對:“請坐———殺雞切細”,“謝謝———四包錫箔”,“冷———好冷得那”,“好———哈老少”。靠著這把折扇,李大人總算過了關。出使歸來,他常為此而津津樂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