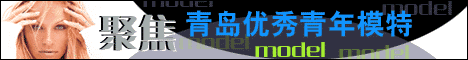美國醫生 音樂伴換人頭
2001-07-25 12:41:02
說換就換,成嗎
下周,美國醫生懷特將在烏克蘭醫學科學院專家們的配合下為來自美國俄亥俄州的一名男子實施人類歷史上的首次換頭手術。該男子名叫威托威茲,19歲時因潛水意外而四肢癱瘓。他的腦袋將被移植到一個腦部死亡的志愿者的身體上。將一個人的頭和另一個人的身體“嫁接”在一起,醫療技術上能不能行得通?社會和周圍的人應該承認新的人頭的身份還是身體的身份呢?會不會引發新的倫理問題?記者為此采訪了上海的相關醫學專家和京滬兩地的社會、倫理學者。
能行嗎?
周良輔教授(華山醫院神經外科主任):到目前為止,國內外的醫學都沒有達到能夠換人頭的水平,其理由有三:干細胞移植還在動物試驗階段,中樞神經再生不可能實現,腦干與脊柱斷掉不會再成活。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當時蘇聯科學家就搞過動物換頭試驗,結果也是不了了之,因為換頭的關鍵是神經細胞再生,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只能宣告換頭試驗失敗。
閔志廉教授(長征醫院腎移植中心主任):換人頭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人體器官移植手術,因為人頭是一個綜合、復雜的人體組成部分,別的不說,光從免疫學上來解釋,現在的醫學技術也是不可能達到換人頭要求的。再則換人頭后思想意識都不是自己的,這種試驗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現在國內是不可能進行這方面試驗的。
江澄川教授(華山醫院神經外科):換人頭光接活血管與骨頭是毫無意義的,最為關鍵的中樞神經細胞卻無法接活,這樣要不了幾小時,換人頭后生命就會結束。以前有報道說動物試驗換頭成功,那也僅僅是10幾個小時就結束生命了。排除倫理道德不說,按照目前的醫學科技,換人頭還不如克隆人的技術成熟,要不然的話,脊柱癱瘓病人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療了。
手術過程
懷特醫生透露說,在換頭手術過程中,醫生們將通過安在頭皮下的電子傳感器密切監視大腦的反應。要換的人頭還用特殊的器件固定在手術臺邊上,確保人頭的狀態穩定,并且順利換到身體上。
當兩個病人完全麻醉之后,兩個手術小組將在輕音樂的伴奏聲中開始史無前例的手術:他們分別切開兩個病人的脖子,小心翼翼地分離出所有的肌肉和組織,仔仔細細地理出頸動脈、頸靜脈和頸神經;緊接著,醫生們得趕緊用能防止血栓形成的肝素包住所有的導管,確保大腦能得到充足的血液循環,這樣的話也就保證大腦不會缺氧。
然后,醫生們將剝離兩個病人脖子脊柱上的骨頭,切開脊髓四周的保護組織;在脊髓和脊柱成功分離之后,其中一個病人的頭就能取下來,立即轉移到與第二個病人人體循環相聯接的試管內,當然第二個腦部已經死亡的病人的頭已經在這之前取掉了。這些至關重要的手術完成后,醫生們將一根一根地清理血管,已經打開的脊柱將用金屬片來縫合固定,至于肌肉和皮膚將逐層縫上。
你愿意嗎?
我不愿意
中國倫理學會秘書長孫春晨認為,頭是人類的思想器官,決定人的具體行為。因此手術成功以后,對于換頭人的身份確認應該不成問題。即頭是誰的,手術后的換頭人就是誰。孫春晨認為既然殘疾人可以做換肢手術,那么將范圍擴大為正常人換一個軀體也是可以理解的。孫認為換頭人一旦在中國出現最大的問題是社會對他的認可與否將在倫理關系上引發一系列問題如同克隆人一樣。由于軀干發生重大變化,換頭人的親人和同事等將對此有一個適應過程。即換頭人的社會倫理關系包括親緣關系難以確認。中國人講究身體的完整,所以中國人對于換頭人還有一個認可的過程。
“如果你遇到這種情況,你會換頭嗎?”記者和孫春晨開玩笑。“我不愿意。”孫回答。
我愿意
上海市倫理學會理事、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胡守鈞對“換人頭”這個新鮮事物持歡迎態度。胡守鈞認為,科學和倫理學都是為人服務的,為人的權利、健康與幸福服務。在人類發展史經常會出現一些當時看來離經叛道的變革,不容于當時的倫理趨向。但倫理應該根據科學的進展進行調整,科學則服務于人。
胡守鈞認為換頭人的出現具有積極的意義。當然,換頭人在實際生活中肯定會遇到不少困難。我堅信如果換頭人在中國出現,社會最終會接受,人們會歡迎這種新技術的發明和推廣,因為它能給人類帶來幸福。
“如果要你做換頭手術,你愿意嗎?”記者問了相同的問題。“如果只有這樣能延續我的生命,我愿意。”胡守鈞的回答毫不遲疑。
背景資料
懷特醫生早在1970年成功地為兩只猴子實施換頭手術,經他換頭的猴子最長的活了8天時間!在最后一次移植猴頭手術中,兩只互換了頭的猴子在手術結束后6個小時就蘇醒了過來。懷特醫生認為給人換頭甚至比給猴子換頭容易得多,因為人的血管和其他人體組織要比猴子的血管和身體組織大得多,而且醫生們給人做手術的經驗比給動物做手術的經驗要豐富得多。